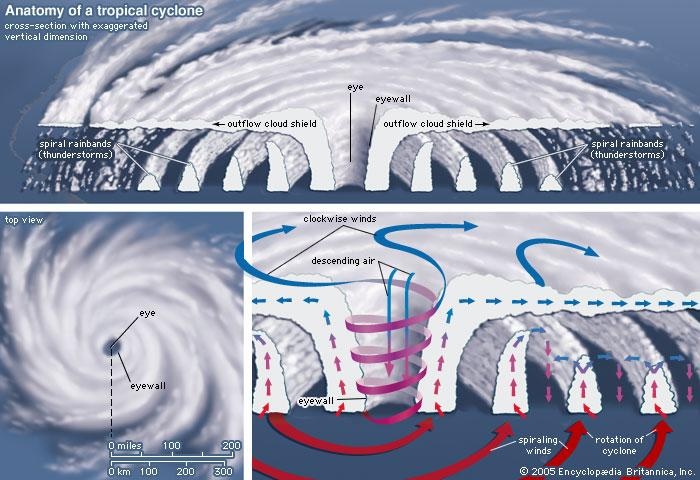飓风的形成需要几个必须条件,首先是海洋靠近赤道夏天在太阳照射下水温升高,大量水分蒸发到空气中形成垂直上行热气流,水分在高空遇冷凝结成雨云形成低空巢。几个间隔有序垂直方向的冷热空气对流在外部气流和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有规律地旋转起来形成风眼,热空气朝风眼旋转,转得越快风眼压力差就越大,压力差越大空气旋转得就越快,这个自激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形成飓风。当风速超过每小时六十三公里称为热带风暴,超过一百一十八公里就是飓风了。飓风分为五级,一级飓风风力每小时一百一十八至一百五十三公里;五级飓风超过每小时二百五十三公里。每年的热带风暴和飓风都有名字,按时间顺序名字的字头以A、B、C、D依次地排下去: 2006 年的名字为Alberto,Beryl, Chris, Debby……这些名字每六年重复使用,那些造成损失巨大的飓风名字例外,比如2012年的Sandy将不会再被使用。
2006年的一号飓风“阿尔伯特”( Alberto)形成时同道者已经安全进入ICW,下一步就是要找个避风小港湾来接受阿尔伯特的考验。这一次又显示了“同道者”吃水浅的优越性,在比佛北面二十海哩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避风港(见题图)。小水湾不大,四周都是长满水草的沼泽地,岸上有高树挡风。因为入口比较浅,吃水深的船进不来,“同道者”独占了整个小水湾。刮大风的时候很忌讳跟别的船离得太近,一旦锚脱位很容易撞船。
“同道者”在同一直线上前后抛下两个锚,同时抛下足够的铁链,为的是如果一个锚脱了位还有另一个锚工作。我们一共有三个锚,猫爪不同形状应付不同海底质地,有适用于沙地,有适用于海藻。我们把船上所有悬挂物件全部取下,遮风棚和遮阳棚也全部放倒。船上装满了足够的食物和水,那严阵以待的劲头真是武装到了牙齿。一切准备就绪,可“阿尔伯特”却姗姗来迟。这位老兄在佛罗里达登陆后不紧不慢地朝北方蹓跶,越走越没精打彩。风前移动得很慢,风力也逐渐在减小。结果让我们在那个小水湾溜溜地恭候了两天。
第一天知道“阿尔伯特”还远着呢,我和侄子开着小汽艇到附近有住家的地方去转转。一位中年美国女人很热情地让我们停靠在她家的浮桥码头上,很友好地攀谈起来。谈得投机她邀请我们去参观她家的养蟹场。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有好几个大水泥池。池子里是不同生长阶段的螃蟹,从很小的蟹苗到硬壳的成蟹。我第一次知道螃蟹也会蜕壳,就像蛇会蜕皮一样。小螃蟹从壳里蜕出来后通身都是软的,软壳蟹仔最嫩最鲜,但这时候的蟹仔也最娇气,环境不合适就不能存活。这位女士给了我一包夭折的软壳蟹仔和硬壳成蟹。她告诉我软壳蟹拿油一煎就能吃。我要给钱,这位女士坚决不收,她说反正这些螃蟹已经死了,不吃也会处理掉。结果我们第一次尝到了软壳蟹的美味,真是鲜美极了。美国南方人真是热情友好。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正在玩拼字游戏( Scrabble),“阿尔伯特”驾到。尽管已经温和多了,这位老兄还是一进门就连哭带嚎,狂风伴着骤雨折腾了大半天。尽管如此,“同道者”的两个锚纹丝没动。有一条加拿大船在我们避风水湾的湾口抛锚,大概因为吃水深进不来,我们眼看着它被吹得左摇右摆,它的马达始终是开着的,以减小锚的受力。我们两条船抛锚位置就差了百来米的距离,可“同道者”却舒舒服服地猫在水湾里,没有任何损失。吃水浅真是太方便了。
2013年11月19日于悉尼。